产品与市场争议不断,相宜本草掉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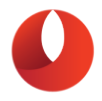 摘要:
编辑 | 余溯出品 | 潮起网「加盟指南」在一众老牌国货护肤品牌中,相宜本草的境况也许是最令人唏嘘的。作为曾年销23亿元的“国货之光”,眼见一些同时期创立的品牌仍在发光发热,但相宜...
摘要:
编辑 | 余溯出品 | 潮起网「加盟指南」在一众老牌国货护肤品牌中,相宜本草的境况也许是最令人唏嘘的。作为曾年销23亿元的“国货之光”,眼见一些同时期创立的品牌仍在发光发热,但相宜... 编辑 | 余溯
出品 | 潮起网「加盟指南」
在一众老牌国货护肤品牌中,相宜本草的境况也许是最令人唏嘘的。
作为曾年销23亿元的“国货之光”,眼见一些同时期创立的品牌仍在发光发热,但相宜本草却在近年来深陷产品安全争议、市场定位模糊与内部治理动荡等多重困境。
甚至,年轻一代消费者对于相宜本草已经越来越陌生。
在国产美妆行业加速分化、头部效应凸显的背景下,这家老牌企业是否已彻底掉队?面对困境,相宜本草能否像一些成功破圈的国货品牌那样为自己找寻到新生路径?
从“本草护肤”到“毒药”标签
不可否认,在品牌巅峰期,相宜本草的品牌力和产品力都非常强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宜本草”四个字的国民度是有的。
而在彼时,相宜本草的核心竞争力是建立于“中草药护肤专家”的差异化定位。然而,近些年频发的成分争议直接让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度遭受重创。
比如在2024年底,相宜本草拳头产品“红景天焕白精华液”被举报违规添加未备案的“犁头尖”成分。
据悉,该成分虽具抗炎功效,但《中华本草》明确记载其“有毒”,且未列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
在此背景下,尽管公司声明称原料合规并指控举报人为被解雇员工,但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产品中确实存在“犁头尖”基因片段及未标注的“凯撒德卡林”、“乌戈宁”等成分,且防腐剂对羟基苯乙酮占比异常高达82.58%,远超行业常规标准。
从“本草护肤”到“毒药”标签,直指相宜本草核心产品力,对于品牌的伤害非常致命。
更令消费者质疑的,是品牌方的危机公关策略。
面对舆论纷争,相宜本草首份声明被删除后仅修改措辞重发,且长期回避提供权威检测报告,却转而以“商誉侵权”为由举报质疑媒体。
这一系列操作让品牌不仅未能平息争议,反而加剧公众对品牌透明度的质疑,直接导致公司2024年双十一销售额仅2亿元,不足另一家与相宜本草同期创立的国货护肤品牌珀莱雅同期14亿元的1/7。
渠道依赖带来困局
深入分析来看,相宜本草在护肤品市场的掉队显然不只是由一次产品翻车或舆论争议所导致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原因的话,绕不开品牌渠道战略的滞后。
从品牌发展历程来看,早期的相宜本草是凭借KA(连锁商超)渠道快速扩张。2011年,公司商超渠道占比已高达76%,但这也成为其后续发展的桎梏。
此后,当珀莱雅、自然堂等竞品纷纷转向CS(化妆品专营店)和电商时,相宜本草仍过度依赖商超,这导致其错失了渠道转型的红利。
至2015年,相宜本草营收较巅峰期已经缩水35%,市场份额排名从第9位暴跌至第20位,或多或少说明了公司在渠道布局上的问题。
此外,虽然近年来相宜本草也曾尝试发力线上,但问题依然显著。
具体表现在,公司过度依赖头部主播,比如在2022年,李佳琦直播间为其贡献了50%销售额,品牌缺乏自营流量沉淀;以及产品价格带竞争力薄弱,品牌主力产品多集中于300元以下区间,与百雀羚、自然堂等同质化竞争严重,而且国际品牌的降价策略进一步挤压了相宜本草的生存空间。
相宜本草还遭遇了高端化尝试失败。
2020年,公司推出高端线“相宜本草·唐”入驻丝芙兰,但因品牌认知固化,高端产品线未能突破价格天花板。
内部治理动荡:IPO折戟与战略摇摆
值得注意的是,频繁的高层变动与战略不连贯,进一步削弱了相宜本草在市场中的的竞争力。
自2012年首次冲击IPO以来,相宜本草已经历三次上市失败,直接诱因包含多个方面。
首先,是管理层动荡。根据相关媒体统计显示,2014-2025年间,相宜本草至少遭遇了9次核心高管离职,包括两任CEO俞巍、张舸均在任职不足一年后出走。
其次,是商业模式的缺陷。据统计,相宜本草经销模式占比超30%,供应链过度依赖代工(90%产品委外生产),且研发投入不足营收1%。在越来越看重产品力、品牌力与服务的时代,相宜本草的这种模式很难构建核心壁垒。
最后,是资本对赌压力。2008年,公司引入今日资本时签订对赌协议,要求营收增速从50%提升至70%-80%。对赌压力之下,导致了公司此后几年的战略激进与资源错配,此后再想翻身不易。
令人玩味的是,面对多重困境,相宜本草创始人封帅虽多次强调“回归产品本质”,但实际动作仍显矛盾:2017年砍掉了年轻子品牌聚焦“红景天”成分,2020年又选择押注数字化与高端化,公司战略摇摆使品牌定位愈发模糊。
相宜本草的掉队背后,是传统国货品牌转型的共性难题。包括相宜本草在内,大量国货品牌都摸索着如何在坚守核心定位与适应市场变革间找到平衡。
虽然相宜本草目前仍具备中草药研发基础与商超渠道资源,但若不能重建信任体系、制定差异化产品战略、提升组织结构稳定性,未来将愈发充满不确定性。
在美妆行业“成分党”、“功效党”主导的新竞争周期中,相宜本草能否重拾“本草护肤”初心,或将决定其最终命运。











